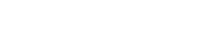第233章 法令终落
“陛下,臣有言奏。”
皇帝话音方落,李显穆已然长身而立,肃然拱手。
眼见李显穆竟然第一时间发言,殿中眾人不禁皆有些好奇,李显穆很少先声夺人,颇有谋定而后动、后发而先至的习惯。
“显穆,你说。”
李显穆理了理袖口的褶皱,在眾人好奇的目光中肃然开口:
“陛下,南京国子监诸士子焚书之事,虽是首例,却绝不会是最后一例,朝廷当谨慎处理,以安天下士子之心。”
“诸士子只焚毁四书章句集注,却高举传世录,说明其本身並未对朝廷离心,只是困顿於理学而不能寸进,是以並无大逆不道的心思。”
“士子谈论时政是自古代就传下来的风气,如今朝廷之上,寒门法令爭吵的不可开交,诸士子乃是寒门子弟,切身所感受,於是对朝政有评论,再正常不过,且言语之间並未涉及陛下以及诸位高官公卿,足见其恭顺守礼。”
“请陛下圣裁!”
朱棣沉吟起来,李显穆所说的三条,大致核心思想,是认为这件事,属於寒门士子在不断地拉锯焦躁中精神难以自持,於是对以吏部尚书蹇义为首的理学当家人產生了强烈的不满,和朝廷本身没有关係。
在这场衝突中,朝廷本是置身事外的角色,衝突的双方是寒门子弟和理学大儒,寒门子弟认为那些理学大儒是断绝他们前路的奸臣!
那些所谓的“公平公正”完全不能服膺寒门子弟的人心。
朱棣若有所思的望了李显穆一眼,一直以来寒门子弟並未有过要被倾泻资源的想法,完全依靠科举成绩来排名,一直都是世人所认可接受的。
寒门子弟过去不能中举中进士,只会觉得是自己能力不足。
可现在寒门子弟的思想发生了变化。
蹇义等人这些年所说的“唯成绩论公平公正”和李显穆等人这些年所说的“应当考虑资源供给的真正的公平公正”,一直爭论不休。
从九天宫闕一直打到民间的各个战场上,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辩论,基本上三分之一的七品以上官员都牵连其中。
双方各执一词,谁也不可能认输。
但辩论的核心本就不是说服对方,而是让旁观的人认可,继而凝聚旁观者的力量。
从如今的结果来看,这场大辩论是李显穆获得了胜利,寒门子弟做出这种事,明显是心中有了极深的不满和怒意。
不能让朝廷替理学背锅!
朱棣几乎在瞬间就做出了正確的选择,甚至都不用再听其他大臣的想法,既然李显穆获得了论战真正的胜利,那他自然要支持胜利的那个人。
在不涉及皇权的时候,皇帝帮谁,谁嬴;谁贏,皇帝帮谁。
“户部尚书方才所说,诸卿可还有不同意见的吗?”朱棣心中虽然有了决断,但还是决定听一听其他人的想法,毕竟这是御前扩大会议,不是李显穆的一言堂。
“陛下,臣有言奏!”吏部尚书蹇义立刻高声出列,眾人皆带著莫名复杂的眼神望向他,心中不由泛起丝好奇和紧张,朱棣也不由坐直了身子,等著看蹇义要如何反驳李显穆。
蹇义偏头望向李显穆,微微嘆口气,而后对著皇帝肃然拱手道:“陛下,圣人说有错则改之,无错则加冕,乃是为圣人之道。
自永乐十七年末以来,朝廷上针对寒门法令之事,爭论不休,诸位大臣各执一词,皆是为朝廷社稷所考虑,难分胜负、难言高低,恰说明,诸位大臣虽然理念不同,可终究都是为国考虑。
如今南京国子监中爆发了如此恶性事件,有些声音认为应当严惩这些士子,臣以为不应当如此,这些士子並未做错什么大事,也並非犯下不可饶恕的过错。
臣建议让这些寒门学子进京,倾听他们的声音,为了社稷安稳,或许真的应该实行寒门法令。”
轰!
殿中几乎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望向吏部尚书蹇义!
殿中陷入了嫉妒的寂静之中。
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他们方才听到了什么?
和李显穆在寒门法令上爭锋相对两年多的蹇义,竟然突然认可了李显穆的想法,选择了认输?
让这些寒门学子进京,不就是彻彻底底的不再阻拦寒门法令了吗?
为什么会如此?
蹇义到底怎么了?
朱棣也以为自己听错了,“蹇卿,你说什么?朕方才好像听到你同意了李显穆的寒门法令。”
蹇义话说出口后也放鬆下来,將那些复杂的思绪收回,认真道:“臣依旧认为寒门法令不够公平,也选不出真正的人才,但如今南京国子监中爆发了如此严重的事件,若是朝廷处理不当,必然引发士林动盪,对大明社稷造成不利的影响,实行寒门法令,是最好的方法。”
在眾人瞠目结舌震惊莫名的时候,李显穆却很是安静,他眼中迸发出精光,三年来,这是他第一次真正认为蹇义算是个对手。
这一手以退为进,绝不简单!
蹇义怕是已经看出来了,放开寒门法令是必然的事情,他若是再执著於此,甚至执著於治那些学子的罪,只会牵连更广,如今迅速和寒门法令之事切割,才能够保护住真正的基本盘。
有趣。
看来这次不能直接將吏部尚书赶下去了,让他在吏部尚书的位置上再坐一段时间吧。
朱棣也明白了蹇义的意思,这件有些出乎他意料的事情打乱了一部分他的计划,他强行平復了心情,又向其他人问道:“蹇卿所说,尔等都听到了,如今户部尚书李显穆和吏部尚书蹇义所言一致,其余诸卿呢?”
寒门法令这件事,一直以来就是李显穆和蹇义相爭,背后折射出的是心理之爭,其余眾人无论心中如何想,自然也不会说了,中立的人不愿意掺和寒门法令和心理之爭,其他人则大佬都选择偃旗息鼓,他们也只能跟著沉默。
“既然诸卿都没有意见,那就按照蹇卿和李卿所言,给天下读书人一个交待。”
皇帝拍了板,其余眾人都再没有意见。
一直离开华盖殿时,许多人还有些懵,在知道了南京焚书之事后,他们都以为今日必然是一场龙爭虎斗,甚至可能有个尚书要为此引咎致仕,可谁都没想到,最后竟然在一团和气中落下了帷幕。
“蹇义这是什么意思?”郑欢走到李显穆身边,疑惑问道:“他怎么突然就认怂了?”
“因为他是个极其聪明的人。”李显穆望著走在一行人之前的蹇义,微微眯著眼淡淡道:“他在寒门法令上的坚持是为了打压心学,可现在他发现,经过这三年,他那一套『公平公正』的说辞已经破產,再坚持下去,理学的根基就要受到影响了。”
郑欢琢磨了下,才恍然大悟,“竟然是这样,能在接受到信件短短时间內,就將这些事想清楚,而拋弃坚持了数年的观点,这蹇义可真是不容小覷。”
李显穆也微微点头,“天下英雄如过江之鯽,这朝堂之上,没有一个人是简单的。”
这里二人在谈论蹇义,走在前面的蹇义也正在被自己派系的人质问,尤其是那些翰林学士,都是理学的究极保守派,在殿上时就忍不住想要开口,还是被蹇义拦住的,如今下朝,他们自然立刻上前询问,语气有些不好。
“蹇尚书,方才在殿中,为何突然改变口风?”
“是啊,那些学子在国子监中焚书,这么大的事情,甚至能定个大不逆的罪名,杀鸡儆猴才是正道!”
“就这么让李显穆做成了寒门法令之事,他岂不是更进一步,显得我理学节节败退。”
眾人围在他身边你一言、我一语的七嘴八舌,吵得蹇义有些头疼,低声怒喝道:“够了!”
他毕竟是当前大明权势最高的吏部尚书,颇有威望和地位,眾人顿时安静下来,但依旧望著蹇义,等著他给出一个解释。
蹇义低声道:“方才李显穆说完那番话后,你们难道没看出来吗?陛下已经心动,用你们的脑子想一想,南京发生了这种事,难道其他地方就不会发生吗?
如果朝廷不能给一个说法,必然会有大批寒门士子怨懟朝廷,甚至怨懟圣上,陛下会拖著自己的声名,依旧支持我们吗?
寒门法令这件事上,我们已经一败涂地了!
再在那里纠缠又有什么用呢?
况且,你们不要忘记了,我们当初是为了反对心学而反对寒门法令的,现在寒门开始反噬,难道你们要將千千万的寒门士子,都推向心学一方吗?
失去了千千万寒门士子,理学的根就要被挖掉了!”
蹇义將根源一讲述,眾人顿时脸色难看的噤声,可却又不得不承认,蹇义说的是正確的,南京之事一发生,寒门法令的爭端就一败涂地,此刻转向,才能最大限度的挽回损失。
眾人不再说话,蹇义有些沉默的望著巍然磅礴的皇宫城楼,这世上的大势总是如此,一旦滑落,便难以再提振。
理学也会如此吗?
曾经日照中天,而今逐渐滑落,在蓬勃发展的心学面前,节节败退。
他有些迷茫。
(本章完)
“陛下,臣有言奏。”
皇帝话音方落,李显穆已然长身而立,肃然拱手。
眼见李显穆竟然第一时间发言,殿中眾人不禁皆有些好奇,李显穆很少先声夺人,颇有谋定而后动、后发而先至的习惯。
“显穆,你说。”
李显穆理了理袖口的褶皱,在眾人好奇的目光中肃然开口:
“陛下,南京国子监诸士子焚书之事,虽是首例,却绝不会是最后一例,朝廷当谨慎处理,以安天下士子之心。”
“诸士子只焚毁四书章句集注,却高举传世录,说明其本身並未对朝廷离心,只是困顿於理学而不能寸进,是以並无大逆不道的心思。”
“士子谈论时政是自古代就传下来的风气,如今朝廷之上,寒门法令爭吵的不可开交,诸士子乃是寒门子弟,切身所感受,於是对朝政有评论,再正常不过,且言语之间並未涉及陛下以及诸位高官公卿,足见其恭顺守礼。”
“请陛下圣裁!”
朱棣沉吟起来,李显穆所说的三条,大致核心思想,是认为这件事,属於寒门士子在不断地拉锯焦躁中精神难以自持,於是对以吏部尚书蹇义为首的理学当家人產生了强烈的不满,和朝廷本身没有关係。
在这场衝突中,朝廷本是置身事外的角色,衝突的双方是寒门子弟和理学大儒,寒门子弟认为那些理学大儒是断绝他们前路的奸臣!
那些所谓的“公平公正”完全不能服膺寒门子弟的人心。
朱棣若有所思的望了李显穆一眼,一直以来寒门子弟並未有过要被倾泻资源的想法,完全依靠科举成绩来排名,一直都是世人所认可接受的。
寒门子弟过去不能中举中进士,只会觉得是自己能力不足。
可现在寒门子弟的思想发生了变化。
蹇义等人这些年所说的“唯成绩论公平公正”和李显穆等人这些年所说的“应当考虑资源供给的真正的公平公正”,一直爭论不休。
从九天宫闕一直打到民间的各个战场上,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辩论,基本上三分之一的七品以上官员都牵连其中。
双方各执一词,谁也不可能认输。
但辩论的核心本就不是说服对方,而是让旁观的人认可,继而凝聚旁观者的力量。
从如今的结果来看,这场大辩论是李显穆获得了胜利,寒门子弟做出这种事,明显是心中有了极深的不满和怒意。
不能让朝廷替理学背锅!
朱棣几乎在瞬间就做出了正確的选择,甚至都不用再听其他大臣的想法,既然李显穆获得了论战真正的胜利,那他自然要支持胜利的那个人。
在不涉及皇权的时候,皇帝帮谁,谁嬴;谁贏,皇帝帮谁。
“户部尚书方才所说,诸卿可还有不同意见的吗?”朱棣心中虽然有了决断,但还是决定听一听其他人的想法,毕竟这是御前扩大会议,不是李显穆的一言堂。
“陛下,臣有言奏!”吏部尚书蹇义立刻高声出列,眾人皆带著莫名复杂的眼神望向他,心中不由泛起丝好奇和紧张,朱棣也不由坐直了身子,等著看蹇义要如何反驳李显穆。
蹇义偏头望向李显穆,微微嘆口气,而后对著皇帝肃然拱手道:“陛下,圣人说有错则改之,无错则加冕,乃是为圣人之道。
自永乐十七年末以来,朝廷上针对寒门法令之事,爭论不休,诸位大臣各执一词,皆是为朝廷社稷所考虑,难分胜负、难言高低,恰说明,诸位大臣虽然理念不同,可终究都是为国考虑。
如今南京国子监中爆发了如此恶性事件,有些声音认为应当严惩这些士子,臣以为不应当如此,这些士子並未做错什么大事,也並非犯下不可饶恕的过错。
臣建议让这些寒门学子进京,倾听他们的声音,为了社稷安稳,或许真的应该实行寒门法令。”
轰!
殿中几乎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望向吏部尚书蹇义!
殿中陷入了嫉妒的寂静之中。
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他们方才听到了什么?
和李显穆在寒门法令上爭锋相对两年多的蹇义,竟然突然认可了李显穆的想法,选择了认输?
让这些寒门学子进京,不就是彻彻底底的不再阻拦寒门法令了吗?
为什么会如此?
蹇义到底怎么了?
朱棣也以为自己听错了,“蹇卿,你说什么?朕方才好像听到你同意了李显穆的寒门法令。”
蹇义话说出口后也放鬆下来,將那些复杂的思绪收回,认真道:“臣依旧认为寒门法令不够公平,也选不出真正的人才,但如今南京国子监中爆发了如此严重的事件,若是朝廷处理不当,必然引发士林动盪,对大明社稷造成不利的影响,实行寒门法令,是最好的方法。”
在眾人瞠目结舌震惊莫名的时候,李显穆却很是安静,他眼中迸发出精光,三年来,这是他第一次真正认为蹇义算是个对手。
这一手以退为进,绝不简单!
蹇义怕是已经看出来了,放开寒门法令是必然的事情,他若是再执著於此,甚至执著於治那些学子的罪,只会牵连更广,如今迅速和寒门法令之事切割,才能够保护住真正的基本盘。
有趣。
看来这次不能直接將吏部尚书赶下去了,让他在吏部尚书的位置上再坐一段时间吧。
朱棣也明白了蹇义的意思,这件有些出乎他意料的事情打乱了一部分他的计划,他强行平復了心情,又向其他人问道:“蹇卿所说,尔等都听到了,如今户部尚书李显穆和吏部尚书蹇义所言一致,其余诸卿呢?”
寒门法令这件事,一直以来就是李显穆和蹇义相爭,背后折射出的是心理之爭,其余眾人无论心中如何想,自然也不会说了,中立的人不愿意掺和寒门法令和心理之爭,其他人则大佬都选择偃旗息鼓,他们也只能跟著沉默。
“既然诸卿都没有意见,那就按照蹇卿和李卿所言,给天下读书人一个交待。”
皇帝拍了板,其余眾人都再没有意见。
一直离开华盖殿时,许多人还有些懵,在知道了南京焚书之事后,他们都以为今日必然是一场龙爭虎斗,甚至可能有个尚书要为此引咎致仕,可谁都没想到,最后竟然在一团和气中落下了帷幕。
“蹇义这是什么意思?”郑欢走到李显穆身边,疑惑问道:“他怎么突然就认怂了?”
“因为他是个极其聪明的人。”李显穆望著走在一行人之前的蹇义,微微眯著眼淡淡道:“他在寒门法令上的坚持是为了打压心学,可现在他发现,经过这三年,他那一套『公平公正』的说辞已经破產,再坚持下去,理学的根基就要受到影响了。”
郑欢琢磨了下,才恍然大悟,“竟然是这样,能在接受到信件短短时间內,就將这些事想清楚,而拋弃坚持了数年的观点,这蹇义可真是不容小覷。”
李显穆也微微点头,“天下英雄如过江之鯽,这朝堂之上,没有一个人是简单的。”
这里二人在谈论蹇义,走在前面的蹇义也正在被自己派系的人质问,尤其是那些翰林学士,都是理学的究极保守派,在殿上时就忍不住想要开口,还是被蹇义拦住的,如今下朝,他们自然立刻上前询问,语气有些不好。
“蹇尚书,方才在殿中,为何突然改变口风?”
“是啊,那些学子在国子监中焚书,这么大的事情,甚至能定个大不逆的罪名,杀鸡儆猴才是正道!”
“就这么让李显穆做成了寒门法令之事,他岂不是更进一步,显得我理学节节败退。”
眾人围在他身边你一言、我一语的七嘴八舌,吵得蹇义有些头疼,低声怒喝道:“够了!”
他毕竟是当前大明权势最高的吏部尚书,颇有威望和地位,眾人顿时安静下来,但依旧望著蹇义,等著他给出一个解释。
蹇义低声道:“方才李显穆说完那番话后,你们难道没看出来吗?陛下已经心动,用你们的脑子想一想,南京发生了这种事,难道其他地方就不会发生吗?
如果朝廷不能给一个说法,必然会有大批寒门士子怨懟朝廷,甚至怨懟圣上,陛下会拖著自己的声名,依旧支持我们吗?
寒门法令这件事上,我们已经一败涂地了!
再在那里纠缠又有什么用呢?
况且,你们不要忘记了,我们当初是为了反对心学而反对寒门法令的,现在寒门开始反噬,难道你们要將千千万的寒门士子,都推向心学一方吗?
失去了千千万寒门士子,理学的根就要被挖掉了!”
蹇义將根源一讲述,眾人顿时脸色难看的噤声,可却又不得不承认,蹇义说的是正確的,南京之事一发生,寒门法令的爭端就一败涂地,此刻转向,才能最大限度的挽回损失。
眾人不再说话,蹇义有些沉默的望著巍然磅礴的皇宫城楼,这世上的大势总是如此,一旦滑落,便难以再提振。
理学也会如此吗?
曾经日照中天,而今逐渐滑落,在蓬勃发展的心学面前,节节败退。
他有些迷茫。
(本章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