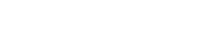“什么?”
“灭韩一战,他屠戮何止十数万,竟然说是自己是大仁大义?简直胡扯!”
淳于越听到这话,差点把自己的八字鬍揪断了,他瞪著一双突眼怒言相斥!
再看扶苏双眼无神,似乎到现在都没有缓过神来,满心的不解和困惑之色,淳于越都有些心疼了。
“公子莫慌,且与臣说来,那血屠是如何诡辩的?”
扶苏先问出了仁义之问,“血屠说,若是不屠城,反而导致诸城復起,强征百姓,则战事继续拉扯加剧,死伤更多,此为仁义乎?”
“又问,诸国攻伐数百年,死伤何止数百万?今我大秦朝夕灭之,陛下若一统天下,即使屠戮百万,岂非仁义之举?”
淳于越冷哼一声,“血屠诡辩!”
他指著案头上的一卷春秋,怒道,“此乃卫文公『启以夏政,疆以戎索』之谬论!昔者武王伐紂,牧野誓师曰『惟恭行天之罚』,何曾以『杀一救百』为仁?”
“若屠城可称仁义,那夏桀焚民为『祭天』、商紂剖心为『正諫』,岂非皆成圣人之举?公子且看——”
他扯开书架上的尚书,“『惟天惠民,惟辟奉天』,周公制礼时早明告天下:
仁政如织帛,纵有千丝万缕之困,岂可用快刀斩乱麻之法?
韩民如丝,秦军如刀,一刀下去看似利落,可断帛之痕终身难补!”
淳于越继续说道,“那血屠说『不屠城则战事绵延』,却忘了《诗经》有云『民亦劳止,汔可小康』——
民求的是『止戈』,非『速死』!
昔者子產治郑,不毁乡校而纳諫,是为『仁术』。
今秦以虎狼之师临韩,却学夏桀『时日曷丧,予及汝偕亡』的暴虐,竟还好意思称『仁义』?”
他又捧起一捧粟米,任由米粒从指缝簌簌落下,砸在竹简刻著的“仁”字上。
“公子且看这粟米——春种时需怜苗惜土,秋收时需轻镰慢割,此乃农夫之仁。
若为求速收而纵火烧田,虽得一时之丰,来年岂有寸土可耕?
秦军屠韩如焚田,今日得十城之速,明日必失天下之心!
那血屠不知『仁者爱人』是『如保赤子』的细护,却当成『快刀斩乱麻』的酷烈,简直是將孔夫子的『仁』字踩在血里碾作泥!”
隨著他慷慨激昂地说著,扶苏的目光也越来越是明亮。
心中的混沌不解,渐渐变得清晰,好似有一道亮光从外界射来,照透了所有的黑暗。
淳于越见此,心中好受了一些,可怜的孩子,差点被血屠蒙蔽。
吾亲身教导良久,才栽育出如此正直的幼苗,怎可被那血屠三言两语给带偏了去?
他嘆了口气,又打开一份礼记,“此篇明言『孟春之月,禁止伐木,无覆巢,无杀孩虫』——天尚且怜幼弱,何况人乎?
今秦军屠城杀卒,与『仲冬斩草除根』的暴政何异?
那血屠若真懂仁义,该学卫武公『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』的慎刑,而非学夏桀『上天弗恤,夏命其卒』的暴虐!
公子且记:真正的仁义是『执柯以伐柯,睨而视之』的循礼。
绝非『以杀止杀』的诡辩!”
扶苏目光明亮,清脆笑道,“正是如此,若是当时先生在那殿上,定能狠狠驳斥那血屠,不至於像吾一般,被血屠三言两语就驳得訥訥无言。”
他觉得丟脸,更觉得自己学问不够精深,应该再深入研究儒学,將儒学学透,融入骨髓血脉,思想深处才行。
淳于越欣慰地笑了,“那血屠只知打仗屠戮,哪里懂得儒家的道理博大精深,恃武力者强於一时,恃德行者才能王於万世啊。”
扶苏此时也轻鬆下来,又说出了自己始终想不明白的那个疑问,“对了先生,那血屠还问了吾一个问题,吾始终想不出答案。”
淳于越慈祥笑著,成竹在胸,“何问?臣为公子解答就是。”
扶苏说道,“那血屠问,若一架马车飞驰之中失控,奔向一幼童,而吾可鞭退马车,但代价是马车之中五人尽死,吾是否要救那幼童?”
“此问有何难?只要……”淳于越说著,突然脸色微变,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刁钻诛心之处。
他深深皱眉,低头沉思起来。
那眉头是越皱越深。
好个血屠,竟敢以此诛心!
他的手指死死掐在案头上面,指节因用力而泛白,却在触及竹简边缘时骤然鬆开。
他张了张嘴,想要说些什么,却又没能发出声音来。
眉头紧皱之际,他的心思越转越快,越转越急,诸多圣人之言在他的脑海之中闪过,又似有无数典籍隨著疾风快速翻页。
无数的理论流淌在心头,却找不到一丝破解之道。
若是他身临其境,只来得及鞭退马车,他该如何抉择?
他握住了尚书,却感到这竹简如同烙铁一般,烫手不已,触电一般鬆开。
“血屠此问……恰似桀紂问比干'天为何有日'..……”
扶苏见到淳于越的表现,刚刚升起来的信心与清明又渐渐回落,“可天为何有日一问,无从回答,也没有意义,救童与否之问,却是真实可能遇到的。”
“若某日行於城中,当真遇到此情此景,依仁义之道,吾该如何抉择?”
“请先生教我!”
此问横亘在扶苏心中,挥之不去。
他实在是迈不过去。
淳于越抬头看到迷茫的扶苏,踉蹌后退几步,袍角扫过书架,竹简噼啪啦坠地。
“若救幼童则五人死...若不救则一童亡...“
他的声音突然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,“这哪里是问仁义...分明是拿秤来称孔夫子的'仁'字能换几斗粟米!“
他想得更多,也更深,“那马车若是秦法的苛政...那幼童便是天下的黔首...可五人难道不是黔首?”
“若不能以杀少救多为仁,难道就视而不见,放任马车碾压幼童,便是仁吗?”
他突然感到浑身无力,儒学最为珍视的惻隱之心,在这一问之中,反倒成了致命的桎梏,让他进退维谷。
上前一步则毁仁,退后一步则灭义。
若是跳出此局,以拉住马车取巧作答,便是避其锋芒,可以说是输给了血屠。
扶苏如何还会重视儒学?
此时,他终於知道扶苏回来的时候,为何是那副模样。
如今就连他,都有点要儒心崩碎。
不行,不能我一个人受难。
“此问……”淳于越斟酌著回答扶苏,“確实有些难度,以臣之学说,尚不能答得完美,需叫上其他儒学博士来共同探討。”
他令门生,“去请博士周青臣来,就说吾有一问不解,需要请教他。”
门生亦是脸色苍白,脚步匆匆地去了。
没多久,周青臣就施施然踏入宫学,一脸笑意盎然,头颅微昂,略有傲然之色。
他看了看扶苏,行礼道,“见过公子。”
而后他又傲然看向淳于越,笑眯眯道,“淳于博士素来精於学问,今日怎的破天荒要问周某问题?”
“哎呀,討论学问,何谈请教?真是不敢当。”
“不过教导公子实在是大事,淳于博士既然遇到了解决不了的学问问题,周某也只能放下手头的事情,立刻赶来了。”
他说著不敢当,嘴上的笑意却是掩藏不住。
都是博士,学的也都是儒学,淳于越却可以教导公子扶苏,好像比他学问精深似的。
这不,遇到问题,还是解决不了,不还得请他周青臣出面解决?
如此一来,高下立判。
公子总该知道,谁才是精通儒学的博士了吧?
淳于越见状暗暗冷笑,现在你笑得开心,且看你一会儿还笑不笑得出来。
“確实是有一个问题难以解决。”
“不久前,公子在殿上遇到了那血屠赵诚,被他以仁义反问,不知如何作答。”
“吾回復了几问,但有一问,实在刁钻,不知该如何反驳才是。”
“哦?”周青臣有些惊讶,也有些不屑,更有些瞧不起淳于越。
一个大儒,竟然被一个打仗的屠子给问住了,真是白学了这许多年的儒学,陛下怎的让他来教导扶苏公子?
“公子莫急,臣来解此问。”
“淳于博士,把此问说与吾听!”
他微昂著头,挺立在那里。
好似天降救星。
扶苏又看到了希望。
淳于越点了点头,说道,“是这样一问——
若一架马车飞驰之中失控,奔向一幼童,而吾可鞭退马车,但代价是马车之中五人尽死,吾是否要救那幼童?”
“自然是……”周青臣刚要作答,突然卡住,意识到了这问题中的巨大陷阱。
他苦思片刻,豁然抬头,惊怖地看向淳于越。
好你个淳于越,自己挨坑还不够,怎么拉著我也来!
这可是在公子面前啊!
你就不能先让公子离开,再叫我来討论?
这可坏了!
刚刚还表现的胸有成竹,如今若是答不上来,岂不一世英名尽毁?
该死,淳于越误我!
可恶的血屠,怎的问出如此诛心之言?
在扶苏那求知的目光之下,他额头隱隱冒汗,心念急转之间,顺著话头说道。
“这有何难,须知《春秋》书『邢迁如归』,看重的是『民视之如归』的本心,而非『得失相抵』的市侩!
那马车如桀紂之暴政,幼童似待哺之黎元。
公子若问『是否救幼童』,便该先问『为何纵马车失控』——正如秦若行仁政,何需用『鞭退马车』的酷烈手段?”
“昔者孔子过匡,匡人围之五日,夫子犹曰『天之未丧斯文也』,是因他知『仁』如日月,纵有浮云蔽目,不可自毁光明以逐暗!”
“仁义之道,正在於『见其生,不忍见其死;闻其声,不忍食其肉』的惻隱。”
“仁如织锦,每一线都需怜惜。义如琢玉,每一刀都需谨慎。那失控的马车正如苛政,真要救幼童,该做的是拉住韁绳而非挥鞭杀人!”
他直接选择跳出此局,退而求其次。
然而扶苏的目光变得有些黯然,他也不傻,若是能拉住韁绳,何必再有此问?
正是因为拉不住韁绳,才要抉择。
而这种情况,他若遇到,如何来得及拉住韁绳?
淳于越更是冷笑,“此问难就难在来不及去拉住韁绳,只能鞭退马车,若以此解,岂不叫那血屠贏了一筹?”
“吾等如何再以仁义教公子?”
周青臣此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,“这……”
“確实如此。”想了想他一咬牙,“吾也答不上来,这样,吾叫伏胜来,伏胜学问精深,定能答得上来!”
“灭韩一战,他屠戮何止十数万,竟然说是自己是大仁大义?简直胡扯!”
淳于越听到这话,差点把自己的八字鬍揪断了,他瞪著一双突眼怒言相斥!
再看扶苏双眼无神,似乎到现在都没有缓过神来,满心的不解和困惑之色,淳于越都有些心疼了。
“公子莫慌,且与臣说来,那血屠是如何诡辩的?”
扶苏先问出了仁义之问,“血屠说,若是不屠城,反而导致诸城復起,强征百姓,则战事继续拉扯加剧,死伤更多,此为仁义乎?”
“又问,诸国攻伐数百年,死伤何止数百万?今我大秦朝夕灭之,陛下若一统天下,即使屠戮百万,岂非仁义之举?”
淳于越冷哼一声,“血屠诡辩!”
他指著案头上的一卷春秋,怒道,“此乃卫文公『启以夏政,疆以戎索』之谬论!昔者武王伐紂,牧野誓师曰『惟恭行天之罚』,何曾以『杀一救百』为仁?”
“若屠城可称仁义,那夏桀焚民为『祭天』、商紂剖心为『正諫』,岂非皆成圣人之举?公子且看——”
他扯开书架上的尚书,“『惟天惠民,惟辟奉天』,周公制礼时早明告天下:
仁政如织帛,纵有千丝万缕之困,岂可用快刀斩乱麻之法?
韩民如丝,秦军如刀,一刀下去看似利落,可断帛之痕终身难补!”
淳于越继续说道,“那血屠说『不屠城则战事绵延』,却忘了《诗经》有云『民亦劳止,汔可小康』——
民求的是『止戈』,非『速死』!
昔者子產治郑,不毁乡校而纳諫,是为『仁术』。
今秦以虎狼之师临韩,却学夏桀『时日曷丧,予及汝偕亡』的暴虐,竟还好意思称『仁义』?”
他又捧起一捧粟米,任由米粒从指缝簌簌落下,砸在竹简刻著的“仁”字上。
“公子且看这粟米——春种时需怜苗惜土,秋收时需轻镰慢割,此乃农夫之仁。
若为求速收而纵火烧田,虽得一时之丰,来年岂有寸土可耕?
秦军屠韩如焚田,今日得十城之速,明日必失天下之心!
那血屠不知『仁者爱人』是『如保赤子』的细护,却当成『快刀斩乱麻』的酷烈,简直是將孔夫子的『仁』字踩在血里碾作泥!”
隨著他慷慨激昂地说著,扶苏的目光也越来越是明亮。
心中的混沌不解,渐渐变得清晰,好似有一道亮光从外界射来,照透了所有的黑暗。
淳于越见此,心中好受了一些,可怜的孩子,差点被血屠蒙蔽。
吾亲身教导良久,才栽育出如此正直的幼苗,怎可被那血屠三言两语给带偏了去?
他嘆了口气,又打开一份礼记,“此篇明言『孟春之月,禁止伐木,无覆巢,无杀孩虫』——天尚且怜幼弱,何况人乎?
今秦军屠城杀卒,与『仲冬斩草除根』的暴政何异?
那血屠若真懂仁义,该学卫武公『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』的慎刑,而非学夏桀『上天弗恤,夏命其卒』的暴虐!
公子且记:真正的仁义是『执柯以伐柯,睨而视之』的循礼。
绝非『以杀止杀』的诡辩!”
扶苏目光明亮,清脆笑道,“正是如此,若是当时先生在那殿上,定能狠狠驳斥那血屠,不至於像吾一般,被血屠三言两语就驳得訥訥无言。”
他觉得丟脸,更觉得自己学问不够精深,应该再深入研究儒学,將儒学学透,融入骨髓血脉,思想深处才行。
淳于越欣慰地笑了,“那血屠只知打仗屠戮,哪里懂得儒家的道理博大精深,恃武力者强於一时,恃德行者才能王於万世啊。”
扶苏此时也轻鬆下来,又说出了自己始终想不明白的那个疑问,“对了先生,那血屠还问了吾一个问题,吾始终想不出答案。”
淳于越慈祥笑著,成竹在胸,“何问?臣为公子解答就是。”
扶苏说道,“那血屠问,若一架马车飞驰之中失控,奔向一幼童,而吾可鞭退马车,但代价是马车之中五人尽死,吾是否要救那幼童?”
“此问有何难?只要……”淳于越说著,突然脸色微变,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刁钻诛心之处。
他深深皱眉,低头沉思起来。
那眉头是越皱越深。
好个血屠,竟敢以此诛心!
他的手指死死掐在案头上面,指节因用力而泛白,却在触及竹简边缘时骤然鬆开。
他张了张嘴,想要说些什么,却又没能发出声音来。
眉头紧皱之际,他的心思越转越快,越转越急,诸多圣人之言在他的脑海之中闪过,又似有无数典籍隨著疾风快速翻页。
无数的理论流淌在心头,却找不到一丝破解之道。
若是他身临其境,只来得及鞭退马车,他该如何抉择?
他握住了尚书,却感到这竹简如同烙铁一般,烫手不已,触电一般鬆开。
“血屠此问……恰似桀紂问比干'天为何有日'..……”
扶苏见到淳于越的表现,刚刚升起来的信心与清明又渐渐回落,“可天为何有日一问,无从回答,也没有意义,救童与否之问,却是真实可能遇到的。”
“若某日行於城中,当真遇到此情此景,依仁义之道,吾该如何抉择?”
“请先生教我!”
此问横亘在扶苏心中,挥之不去。
他实在是迈不过去。
淳于越抬头看到迷茫的扶苏,踉蹌后退几步,袍角扫过书架,竹简噼啪啦坠地。
“若救幼童则五人死...若不救则一童亡...“
他的声音突然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,“这哪里是问仁义...分明是拿秤来称孔夫子的'仁'字能换几斗粟米!“
他想得更多,也更深,“那马车若是秦法的苛政...那幼童便是天下的黔首...可五人难道不是黔首?”
“若不能以杀少救多为仁,难道就视而不见,放任马车碾压幼童,便是仁吗?”
他突然感到浑身无力,儒学最为珍视的惻隱之心,在这一问之中,反倒成了致命的桎梏,让他进退维谷。
上前一步则毁仁,退后一步则灭义。
若是跳出此局,以拉住马车取巧作答,便是避其锋芒,可以说是输给了血屠。
扶苏如何还会重视儒学?
此时,他终於知道扶苏回来的时候,为何是那副模样。
如今就连他,都有点要儒心崩碎。
不行,不能我一个人受难。
“此问……”淳于越斟酌著回答扶苏,“確实有些难度,以臣之学说,尚不能答得完美,需叫上其他儒学博士来共同探討。”
他令门生,“去请博士周青臣来,就说吾有一问不解,需要请教他。”
门生亦是脸色苍白,脚步匆匆地去了。
没多久,周青臣就施施然踏入宫学,一脸笑意盎然,头颅微昂,略有傲然之色。
他看了看扶苏,行礼道,“见过公子。”
而后他又傲然看向淳于越,笑眯眯道,“淳于博士素来精於学问,今日怎的破天荒要问周某问题?”
“哎呀,討论学问,何谈请教?真是不敢当。”
“不过教导公子实在是大事,淳于博士既然遇到了解决不了的学问问题,周某也只能放下手头的事情,立刻赶来了。”
他说著不敢当,嘴上的笑意却是掩藏不住。
都是博士,学的也都是儒学,淳于越却可以教导公子扶苏,好像比他学问精深似的。
这不,遇到问题,还是解决不了,不还得请他周青臣出面解决?
如此一来,高下立判。
公子总该知道,谁才是精通儒学的博士了吧?
淳于越见状暗暗冷笑,现在你笑得开心,且看你一会儿还笑不笑得出来。
“確实是有一个问题难以解决。”
“不久前,公子在殿上遇到了那血屠赵诚,被他以仁义反问,不知如何作答。”
“吾回復了几问,但有一问,实在刁钻,不知该如何反驳才是。”
“哦?”周青臣有些惊讶,也有些不屑,更有些瞧不起淳于越。
一个大儒,竟然被一个打仗的屠子给问住了,真是白学了这许多年的儒学,陛下怎的让他来教导扶苏公子?
“公子莫急,臣来解此问。”
“淳于博士,把此问说与吾听!”
他微昂著头,挺立在那里。
好似天降救星。
扶苏又看到了希望。
淳于越点了点头,说道,“是这样一问——
若一架马车飞驰之中失控,奔向一幼童,而吾可鞭退马车,但代价是马车之中五人尽死,吾是否要救那幼童?”
“自然是……”周青臣刚要作答,突然卡住,意识到了这问题中的巨大陷阱。
他苦思片刻,豁然抬头,惊怖地看向淳于越。
好你个淳于越,自己挨坑还不够,怎么拉著我也来!
这可是在公子面前啊!
你就不能先让公子离开,再叫我来討论?
这可坏了!
刚刚还表现的胸有成竹,如今若是答不上来,岂不一世英名尽毁?
该死,淳于越误我!
可恶的血屠,怎的问出如此诛心之言?
在扶苏那求知的目光之下,他额头隱隱冒汗,心念急转之间,顺著话头说道。
“这有何难,须知《春秋》书『邢迁如归』,看重的是『民视之如归』的本心,而非『得失相抵』的市侩!
那马车如桀紂之暴政,幼童似待哺之黎元。
公子若问『是否救幼童』,便该先问『为何纵马车失控』——正如秦若行仁政,何需用『鞭退马车』的酷烈手段?”
“昔者孔子过匡,匡人围之五日,夫子犹曰『天之未丧斯文也』,是因他知『仁』如日月,纵有浮云蔽目,不可自毁光明以逐暗!”
“仁义之道,正在於『见其生,不忍见其死;闻其声,不忍食其肉』的惻隱。”
“仁如织锦,每一线都需怜惜。义如琢玉,每一刀都需谨慎。那失控的马车正如苛政,真要救幼童,该做的是拉住韁绳而非挥鞭杀人!”
他直接选择跳出此局,退而求其次。
然而扶苏的目光变得有些黯然,他也不傻,若是能拉住韁绳,何必再有此问?
正是因为拉不住韁绳,才要抉择。
而这种情况,他若遇到,如何来得及拉住韁绳?
淳于越更是冷笑,“此问难就难在来不及去拉住韁绳,只能鞭退马车,若以此解,岂不叫那血屠贏了一筹?”
“吾等如何再以仁义教公子?”
周青臣此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,“这……”
“確实如此。”想了想他一咬牙,“吾也答不上来,这样,吾叫伏胜来,伏胜学问精深,定能答得上来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