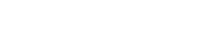手机还在响,丁义珍没接,只是把它翻了个面扣在副驾座上。
车窗外的雨已经停了,路面上的水洼映著灰白的天光,像一块块没擦乾净的玻璃。
他看了眼时间,七点二十三分,机场高速的车流开始多了起来。
周叔的电话半小时前就打过来,说车在航站楼外等著,走贵宾通道,不碰记者。他点头,没多问。这种事,周叔比他熟。
车进党校东门的时候,他才把手机塞回兜里。门卫看了眼证件,抬杆放行。沿路两排梧桐,叶子被前夜的雨打落了一地,扫得不彻底,车轮碾过去,沙沙响。
宿舍是三號楼二楼,单人单间,空调能用,热水稳定。他放下行李,拉开窗帘。楼下是个小操场,几个穿运动服的人在慢跑,动作规整得像广播体操。
报到时,工作人员看了眼名单,又看了他一眼:“您就是丁县?住三楼的套间已经准备好了。”
“不用,这间就行。”
“可这是普通学员房。”
“我来听课,又不是来住宾馆的。”
对方愣了下,没再坚持。递来一叠资料,课程表、纪律守则、作息时间,还有一本《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手册》。他翻了两页,全是標准话术,但字里行间透著一股“你们都得听”的劲儿。
开班仪式在礼堂。一百多人,清一色衬衫西裤,年纪多在三十五到四十五之间。
他坐在后排靠窗的位置,旁边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,自我介绍说是某部委的调研员,姓李。
“丁书记,抗洪的事我看了报导,真不容易。”
“不是我一个人的事。”
“但你是代表。”
他没接这话。台上领导正讲“新时代干部的使命担当”,他听著听著,脑子里却跳出老李蹲在冲床边调模具的样子,还有那个哼著歌拧绳索的年轻司机。
第一堂课是政治理论,讲“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”。教授站在讲台前,语速平稳,逻辑严密,可丁义珍听著听著,总觉得哪不对。不是內容错,是听著像在讲別人的事。
课间休息,几个学员聚在门口抽菸。有人提到他:“听说这位是从县里直接上来的,救灾先进个人。”
“县级干部进这班,少见。”
“估计是上面有人。”
他走过去接水,假装没听见。水有点烫,他没吹,直接喝了一口。
下午分组討论,他被分到第三组,主题是“政策执行中的基层困境”。轮到他发言时,他没讲大道理,只说了两件事:一是抗洪那晚,变压器进水,他要发电机,周叔调货机空运;二是工人打包救灾物资,他当场结算双倍工资。
“所以你的意思是,靠个人关係和临时决断解决问题?”有人问。
“我不是说这方法好,我是说,政策到基层,常常卡在『最后一公里』。设备坏了,等审批三天,厂子就淹了;工人不干活,等开会研究,货就发不出去。”
戴眼镜的李调研员接话:“所以你主张放权?”
“我不主张什么,我只想说,弓要是太硬,箭反而射不远。政策是箭,执行是弓,弓得有弹性。”
会议室安静了几秒。有人低头记笔记,有人交换眼神。
第二天早上六点,他起床跑步。操场上人不多,他沿著跑道慢跑,边跑边想那台冲床重新响起来的声音。
回到宿舍,掏出手机,翻出抗洪期间的调度记录:抽水设备调配时间、民兵连出动顺序、物流发车节点。他把这些数据整理成表格,標出关键决策点。
【记住全网最快小説站 追书认准 101 看书网,101????????????.??????超省心 】
中午吃饭,碰上同组的几个学员。有人问:“你这些数据,打算用来干啥?”
“上课用。老师讲『执行效率』,我就拿这个当案例。”
“你这是把实战搬进课堂啊。”
“基层哪有那么多理论?问题来了,就得动。”
政治理论课第三天,教授讲到“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產力”。下课前,丁义珍举手提问:“老师,如果一项政策理论上完美,但在基层执行时导致企业停產、工人失业,那它算不算真正解放了生產力?”
教授没立刻回答,反而笑了:“这个问题,来自实践,很好。我们下次课可以专门討论。”
他点头坐下。旁边李调研员小声说:“你这问题,够狠。”
“不是狠,是真遇到过。”
晚上十点,他还在写笔记。窗外黑了,楼道灯亮著,偶尔有脚步声。他翻到《毛泽东选集》里那句“从群眾中来,到群眾中去”,想起王大陆那天劝他的话:“別把县当成战场,咱们是搞建设,不是打衝锋。”
他停下笔,盯著这句话看了很久。
然后在本子上写下:“治理不是打仗,是种树。种下去,得让人乘凉。”
又翻一页,写:“政策温度 = 执行精度 x 群眾感受度。”
第二天小组会上,他把这两句念了出来。有人笑:“这公式挺新鲜。”
“不是公式,是感觉。发电机空运那晚,我算过成本,三倍市价。可要是机器泡坏了,损失是十倍。帐能算清,人心算不清。”
李调研员说:“你这是把人情世故当管理工具?”
“不是工具,是底线。工人愿意加班,是因为知道干完活当场能拿钱。政策要是连这点都保不住,再漂亮也没用。”
討论到中午,食堂吃饭时,有人主动坐到他旁边:“你们县那个红薯粉,我查了,网上销量涨得挺快。”
“刚起步。”
“可你把救灾故事印在箱子上,这招聪明。”
“不是为了卖货,是为了还帐。”
对方愣了下:“还帐?”
“洪水时,外县送了我们三百包米。现在我们能產了,不还,说不过去。”
那人没再说话,低头扒饭。
一周后,课程进入“领导艺术”模块。教授讲“权威与信任的构建”,举了几个经典案例。丁义珍听完,举手说:“我有个问题——如果一个领导在危机中靠非常手段稳住局面,但这些手段本身不合规,事后该怎么评价?”
教室安静了。
教授看著他:“你有具体例子?”
“比如,临时徵用企业设备,没走审批;给工人发双倍工资,没经过財政流程。事急从权,可权从何来?”
教授沉吟片刻:“这確实是个难题。制度是刚性的,现实是弹性的。我们不能因权废制,也不能因制误事。”
他点头:“所以我现在在想,怎么让弹性不越界,又不让刚性压死人。”
课后,教授单独留他聊了二十分钟。临走时说:“你这些思考,建议写进结业论文。来自泥土的思考,最有分量。”
他回到宿舍,翻开笔记本,把这几天记的东西重新梳理。突然看到手机相册里那张螺丝的照片——沾著泥,打了“抗洪水记”钢印。
他盯著看了会儿,合上手机。
窗外,几个学员在打羽毛球,球拍声清脆。他站起身,走到阳台,风吹在脸上,有点凉。
楼下公告栏贴了新通知:下周將组织学员赴基层调研,地点待定。
他看了一会儿,转身回屋,打开电脑,新建了个文档。
標题还没想好,只打了第一行字:“政策往下走,得先听地里的声音。”
车窗外的雨已经停了,路面上的水洼映著灰白的天光,像一块块没擦乾净的玻璃。
他看了眼时间,七点二十三分,机场高速的车流开始多了起来。
周叔的电话半小时前就打过来,说车在航站楼外等著,走贵宾通道,不碰记者。他点头,没多问。这种事,周叔比他熟。
车进党校东门的时候,他才把手机塞回兜里。门卫看了眼证件,抬杆放行。沿路两排梧桐,叶子被前夜的雨打落了一地,扫得不彻底,车轮碾过去,沙沙响。
宿舍是三號楼二楼,单人单间,空调能用,热水稳定。他放下行李,拉开窗帘。楼下是个小操场,几个穿运动服的人在慢跑,动作规整得像广播体操。
报到时,工作人员看了眼名单,又看了他一眼:“您就是丁县?住三楼的套间已经准备好了。”
“不用,这间就行。”
“可这是普通学员房。”
“我来听课,又不是来住宾馆的。”
对方愣了下,没再坚持。递来一叠资料,课程表、纪律守则、作息时间,还有一本《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手册》。他翻了两页,全是標准话术,但字里行间透著一股“你们都得听”的劲儿。
开班仪式在礼堂。一百多人,清一色衬衫西裤,年纪多在三十五到四十五之间。
他坐在后排靠窗的位置,旁边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,自我介绍说是某部委的调研员,姓李。
“丁书记,抗洪的事我看了报导,真不容易。”
“不是我一个人的事。”
“但你是代表。”
他没接这话。台上领导正讲“新时代干部的使命担当”,他听著听著,脑子里却跳出老李蹲在冲床边调模具的样子,还有那个哼著歌拧绳索的年轻司机。
第一堂课是政治理论,讲“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”。教授站在讲台前,语速平稳,逻辑严密,可丁义珍听著听著,总觉得哪不对。不是內容错,是听著像在讲別人的事。
课间休息,几个学员聚在门口抽菸。有人提到他:“听说这位是从县里直接上来的,救灾先进个人。”
“县级干部进这班,少见。”
“估计是上面有人。”
他走过去接水,假装没听见。水有点烫,他没吹,直接喝了一口。
下午分组討论,他被分到第三组,主题是“政策执行中的基层困境”。轮到他发言时,他没讲大道理,只说了两件事:一是抗洪那晚,变压器进水,他要发电机,周叔调货机空运;二是工人打包救灾物资,他当场结算双倍工资。
“所以你的意思是,靠个人关係和临时决断解决问题?”有人问。
“我不是说这方法好,我是说,政策到基层,常常卡在『最后一公里』。设备坏了,等审批三天,厂子就淹了;工人不干活,等开会研究,货就发不出去。”
戴眼镜的李调研员接话:“所以你主张放权?”
“我不主张什么,我只想说,弓要是太硬,箭反而射不远。政策是箭,执行是弓,弓得有弹性。”
会议室安静了几秒。有人低头记笔记,有人交换眼神。
第二天早上六点,他起床跑步。操场上人不多,他沿著跑道慢跑,边跑边想那台冲床重新响起来的声音。
回到宿舍,掏出手机,翻出抗洪期间的调度记录:抽水设备调配时间、民兵连出动顺序、物流发车节点。他把这些数据整理成表格,標出关键决策点。
【记住全网最快小説站 追书认准 101 看书网,101????????????.??????超省心 】
中午吃饭,碰上同组的几个学员。有人问:“你这些数据,打算用来干啥?”
“上课用。老师讲『执行效率』,我就拿这个当案例。”
“你这是把实战搬进课堂啊。”
“基层哪有那么多理论?问题来了,就得动。”
政治理论课第三天,教授讲到“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產力”。下课前,丁义珍举手提问:“老师,如果一项政策理论上完美,但在基层执行时导致企业停產、工人失业,那它算不算真正解放了生產力?”
教授没立刻回答,反而笑了:“这个问题,来自实践,很好。我们下次课可以专门討论。”
他点头坐下。旁边李调研员小声说:“你这问题,够狠。”
“不是狠,是真遇到过。”
晚上十点,他还在写笔记。窗外黑了,楼道灯亮著,偶尔有脚步声。他翻到《毛泽东选集》里那句“从群眾中来,到群眾中去”,想起王大陆那天劝他的话:“別把县当成战场,咱们是搞建设,不是打衝锋。”
他停下笔,盯著这句话看了很久。
然后在本子上写下:“治理不是打仗,是种树。种下去,得让人乘凉。”
又翻一页,写:“政策温度 = 执行精度 x 群眾感受度。”
第二天小组会上,他把这两句念了出来。有人笑:“这公式挺新鲜。”
“不是公式,是感觉。发电机空运那晚,我算过成本,三倍市价。可要是机器泡坏了,损失是十倍。帐能算清,人心算不清。”
李调研员说:“你这是把人情世故当管理工具?”
“不是工具,是底线。工人愿意加班,是因为知道干完活当场能拿钱。政策要是连这点都保不住,再漂亮也没用。”
討论到中午,食堂吃饭时,有人主动坐到他旁边:“你们县那个红薯粉,我查了,网上销量涨得挺快。”
“刚起步。”
“可你把救灾故事印在箱子上,这招聪明。”
“不是为了卖货,是为了还帐。”
对方愣了下:“还帐?”
“洪水时,外县送了我们三百包米。现在我们能產了,不还,说不过去。”
那人没再说话,低头扒饭。
一周后,课程进入“领导艺术”模块。教授讲“权威与信任的构建”,举了几个经典案例。丁义珍听完,举手说:“我有个问题——如果一个领导在危机中靠非常手段稳住局面,但这些手段本身不合规,事后该怎么评价?”
教室安静了。
教授看著他:“你有具体例子?”
“比如,临时徵用企业设备,没走审批;给工人发双倍工资,没经过財政流程。事急从权,可权从何来?”
教授沉吟片刻:“这確实是个难题。制度是刚性的,现实是弹性的。我们不能因权废制,也不能因制误事。”
他点头:“所以我现在在想,怎么让弹性不越界,又不让刚性压死人。”
课后,教授单独留他聊了二十分钟。临走时说:“你这些思考,建议写进结业论文。来自泥土的思考,最有分量。”
他回到宿舍,翻开笔记本,把这几天记的东西重新梳理。突然看到手机相册里那张螺丝的照片——沾著泥,打了“抗洪水记”钢印。
他盯著看了会儿,合上手机。
窗外,几个学员在打羽毛球,球拍声清脆。他站起身,走到阳台,风吹在脸上,有点凉。
楼下公告栏贴了新通知:下周將组织学员赴基层调研,地点待定。
他看了一会儿,转身回屋,打开电脑,新建了个文档。
標题还没想好,只打了第一行字:“政策往下走,得先听地里的声音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