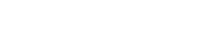第306章 帝师
庭前开又落,春去秋来岁岁年。
数年时光,匆匆而过,如今已然是宣德九年。
皇帝正春秋鼎盛。
内阁首辅威压天下。
外无强敌、内有贤臣,上有明君、宇内澄清,大明煌煌然如日上中天,俨然有追汉唐之威仪。
皇城以南,宫门以北,有黑瓦青砖,正六间堂屋,坐北朝南,正是如今大明政务的副核心文渊阁。
李显穆权势日盛,六部之权被内阁侵蚀愈重,如今民间已然称之为“内阁为相,而六部属焉”,即,六部是内阁的下属,是为内阁办事的。
虽然有所夸张,但却充分展示了如今内阁的权势。
五年前,内阁大学士黄淮、金幼孜都离开了内阁,而后又补入了一位尚书、一位右都御史。
二品高官入内阁,为群辅,位在首辅、次辅之下,这等境遇,让天下士林为之震动。
对内阁愈发敬畏。
文渊阁占地愈多,却仍然稍显逼仄,概因其文书之多,远胜往昔。
外间文书小吏颇为繁忙,一迭迭奏章被分门别类抱进抱出,虽不乱,却匆匆,幸好制度明确,颇有条理,才极少有错漏之事。
首辅独占一间,其后左右各坐二三人,各理其事,若有疑难,则由首辅核准裁决,若有大事则众人齐聚文渊阁中堂,进行商议,以定票拟。
文渊阁中堂,李显穆端坐长桌之后,左右各堆着一堆奏章,不时有书吏将右侧的奏章带走,又不断有书吏往左侧添上新的奏章。
许是有些累,李显穆停下笔,轻轻揉了揉眼睛,站起身向外走去,入目所见,皆是红墙黄瓦,富丽堂皇。
仰首望天,高高的宫墙衬的这偌大皇宫如一口四方井,将人紧紧束缚在这里。
他眉眼间带着消散不去的寒意厉色,仿佛深深刻在心头。
“永不曾停下啊。”
李显穆微微感慨着,治理天下当真是艰难,永远都有层出不穷的问题,解决了一个问题,立刻就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冒出来。
“元辅。”
有书吏自身后来,轻声呼唤。
李显穆回身望去,书吏谦卑躬身,垂首抱拳,“方才御前总管来传口谕,陛下请诸位学士至华盖殿,有要事相商。”
李显穆微微点头,示意自己知晓,抬眼看去,另外几位内阁大学士已然从各堂阁中走出,几人汇在一起,往华盖殿而去。
入殿后,一看皇帝脸色,几人就知道不是坏事。
皇帝朱瞻基立在上首,数年皇帝生涯,让他眉宇间多出几分凛然不可侵犯之意。
数年以来,李显穆固然威势愈盛,但皇帝更是威严盛隆,在政事上,他大部分委任给大臣,只参与重要决策。
但在军事上,他丝毫不假手他人,两次御驾亲征北巡,让瓦剌、鞑靼望风而逃。
又整治三大营,在军队中安插忠诚于自己的亲信,用联姻等方式笼络高级勋贵,牢牢握着兵权,是真正的实权皇帝。
见众人走进,朱瞻基当即命内侍给李显穆,以及上了年纪的杨士奇搬椅子过来,不多时,六部尚书、左右都御史等人也入了殿中,基本上大明朝中枢高级官员,齐聚一堂。
见人到齐了,朱瞻基当即笑道:“今日召诸卿前来,是有一件比较重要的事,皇太子年岁渐长,朕、太后、皇后,都想着让他出阁读书,不知诸卿可有什么想法?”
殿中群臣闻言顿时神色皆一凛,唯有李显穆微微眯起了眼。
皇太子朱祁镇实际上可以算是宣德二年生人,如今是宣德九年,满打满算,宣德九年过完,他八岁整,的确是可以出阁读书的年纪。
群臣之所以如此紧张,自然是因为,皇子出阁读书之事,涉及到未来的权力之争。
若是能提前在太子这里布局,或许未来就有奇效。
虽然皇帝现在春秋鼎盛,但提前落子总是没错的。
无论内阁还是部堂,都有人蠢蠢欲动。
倘若能成为太子师,那未来就是帝师,有了这重身份,未来未必不能和首辅李显穆一比。
李显穆则认为自己大概率做不成这个帝师。
除非皇帝一定要选择他。
但皇帝大概率也不会选择他。
朱瞻基虽然极度信任他,但这种信任依旧是有上限的,作为一个登基九年、十年的皇帝,平衡朝堂实力刻在他的骨子里。
就比如,他可以让李显穆放开手脚去做事,给予一切支持,但却不可能让李显穆把反对派全部处理掉。
是以李显穆不曾先开口。
李显穆对朱瞻基是有些误会的。
朱瞻基是真的考虑过让李显穆做皇太子老师的,但是又想到李显穆平日里已然很忙,不一定能有时间教导皇太子蒙学,于是最终放弃了。
打算等到皇太子十五岁左右,能正式开始接触政事,再由李显穆教导,当初他也是这个年龄,才由李显穆开始正式教导。
礼部尚书径直出言道:“陛下,臣以为当选饱学鸿儒,为皇太子教授,先以圣人之言,定其初生之心神,以正其魂、其骨。”
李显穆眉头缓缓舒展。
饱学鸿儒!
礼部尚书说出这四个字,就是为了把李显穆排除出帝师行列,因为李显穆虽然是圣人子弟,也曾经连中小三元、大三元,但他还真的算不上鸿儒,而一直以经世致用的面容面对天下。
从他出世以来,从来没有在学术方面发表过任何一篇文章,也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一场经典讨论,甚至在传播心学这方面,他所做的也是利用政治影响力来推动。
真正传播心学思想的一直都是他师兄王艮。
虽然,这都是李显穆装的,他是故意不在学术上发挥天赋,要知道,在李祺使用半圣之姿后,李显穆最强的一项天赋就是学术,政治天赋反而稍逊。
但世人不知道。
真以为他不擅长这方面。
李显穆自然不可能现在暴露,于是微微垂下头去,他不会去争皇太子的帝师资格。
没有意义。
成为帝师,是为了潜移默化的向未来的皇帝施加影响力,可如今已然是宣德九年,明年朱瞻基就会驾崩,一年时间,根本来不及施加什么影响力。
后宫可是有太后和皇后的,再怎么比,难道还能比得过那两位吗?
未来皇帝的态度,实际上取决于太后、皇后的态度。
李显穆所考虑的实际上就是后来的张居正和李太后合作的模式,皇帝服从太后,于是皇权在李太后手中,李太后再通过制度,把权力让渡给内阁首辅。
一开始高拱,但是高拱失去了李太后的信任,于是灰溜溜的被赶回了老家,张居正则被信任,得以掌权,这就是万历年间的权力运作模式。
李显穆预计,若是皇帝朱瞻基驾崩,极大概率会将政权移交给张太后和孙皇后,而后设立辅政大臣。
那他真正该施加影响力的,应当是张太后,孙皇后大概率是难以合作的,毕竟现在孙光宗还在南京城里关着呢。
“鸿儒吗?”
皇帝重复了一句,轻轻点头,“是应当寻鸿儒教导,除了鸿儒之外,朕也会亲自教导他,还要为他多选几个师傅,当初太宗皇帝为朕选了很多师傅,才有朕今日,如今朕也要让皇太子,文武双全,未来能克继大统。”
见到自己的意见被采纳,礼部尚书顿时欣喜,当即便举出几个例子,皆是在朝野之中,颇有盛名的鸿儒。
见李显穆一直沉默,其余人也忍不住开始推荐自己认为合适的人选。
“老师觉得呢?”
皇帝一开口问李显穆,其余人顿时安静了下来,李显穆平静着、施施然道:“皇太子年纪尚幼,心性不定,如今所学的应当是正心之法,使皇太子未来能有慨然于振作天下之心。
国朝选士,是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。
培养君王则更是如此,让隋朝二世而亡的隋炀帝,并不是没有才华、并不是没有才能,可却没有德行,于是肆虐天下,最终导致国败社稷亡。
臣并无太多推荐,只请陛下以此选士。”
朱瞻基含笑朗声道:“老师所言,朕都记在心中了,当真是明言之理,诸位卿家今日可再推荐些人,朕思索一番再说。”
殿中群臣又开始分别推荐自己派系,或者和自己有关系的人。
当然,这些被推荐的人,其实大多数都没问题,教个七八岁的小屁孩而已,以这些人的水平,只要智力中等偏上,教出个举人、进士,都没问题。
……
朱瞻基带着一大群推荐名字回到了后宫,将今日之事讲给孙皇后,又将朝臣所推荐的人选一一讲给孙皇后听。
恰在此时,朱祁镇也进了皇后宫中,拜过了皇帝和皇后,颇为好奇的问道:“父皇、母后,这是什么?”
朱瞻基摸摸朱祁镇的头,温声道:“这是父皇给你找的未来老师,日后你就要跟着他们读书学习了。”
“里面可有内阁首辅守正公吗?”
“哦?你想跟着守正公学习?”
朱瞻基倒是有些惊讶,谁知朱祁镇连忙摇了摇头,如同一只拨浪鼓一样,连声拒绝道:“儿子不要跟着守正公学习,千万不要。”
这下朱瞻基直接皱起了眉头,“儿子,你为什么不想跟着守正公学习,他虽然不是鸿儒,但才能是毋庸置疑的。”
朱祁镇有些不好意思道:“他太凶了,每次在宫中、宴会上见到他,都凶凶的,不苟言笑,让人很害怕。”
朱瞻基闻言一愣,紧皱了眉头顿时舒展开,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,他万万想不到会是这个原因。
本来还以为是有人和皇太子说了些什么,他虽然暂时放弃了让李显穆当帝师的打算,但维持两人之间良好的关系,保持初步的信任,还是要做的。
他自然知道自己儿子说的很正常。
李显穆这些年在朝廷之上,厉行澄清吏治,这可不是一件老好人能做出来的事,是以终日不苟言笑、威严日盛,顾盼之间,回眸之时,满是压迫,即便是那张帅脸也救不了这种精神上的威压。
平日里,纵然是其他的官吏们也畏之如虎,更不要说朱祁镇这个小孩了,怕是见过一次之后,怕是能止小孩夜啼。
孙皇后见朱祁镇所说,反而显出笑容来,“既然皇儿不愿意,那就不让阁老当老师,我大明能人辈出,难道还找不出几个能教得了皇儿的人吗?
况且,陛下才是这世上最好的老师,皇儿跟在陛下的身边长大,就像是陛下跟在太宗皇帝身边长大,未来必定是一代明君,和我大明的历代先帝一样。”
听孙皇后提起太宗皇帝,朱瞻基顿时陷入了回忆之中,他这一身本事,有七成都是太宗皇帝教的,爷孙两的感情是真的好。
他轻轻摸了摸朱祁镇的脑袋,眼中满是柔色,“父皇为好好教你的,未来还要把大明江山都交到你的手中。”
朱祁镇闻言顿时高高挺起了胸膛,中气十足的说道:“父皇母后放心,儿子日后必然会向列祖列宗学习,北御蒙古,南镇诸夷,儿子以后也要想太宗皇帝和父皇那样,御驾亲征,让瓦剌和鞑靼知道,什么叫做天威不可冒犯!”
朱瞻基听着朱祁镇这中气十足,又颇有志向的小儿言语,顿时大声笑起来,边笑边道:“好,朕的儿子果然像朕,有志气,当初朕十几岁就跟着太宗皇帝北征,等你十几岁的时候,朕也带着你北巡,教给你如何派兵布阵,也许日后,你也能成为太宗皇帝那样的将军皇帝呢。”
不得不说,良好的传统是会继承的。
大唐每一任皇帝都梦想成为唐太宗,希望能够再现贞观盛世。
而大明朝,朱棣五征蒙古带来的影响力余波,十年后仍旧经久不散,朱瞻基两次北巡,在长城外和蒙古对拼,便是深受朱棣的影响。
如今一个八岁稚童,眼见父亲、祖宗的丰功伟绩,也以御驾亲征,击破蒙古为志向。
当真是,薪火相传,以为圣光!
(本章完)
庭前开又落,春去秋来岁岁年。
数年时光,匆匆而过,如今已然是宣德九年。
皇帝正春秋鼎盛。
内阁首辅威压天下。
外无强敌、内有贤臣,上有明君、宇内澄清,大明煌煌然如日上中天,俨然有追汉唐之威仪。
皇城以南,宫门以北,有黑瓦青砖,正六间堂屋,坐北朝南,正是如今大明政务的副核心文渊阁。
李显穆权势日盛,六部之权被内阁侵蚀愈重,如今民间已然称之为“内阁为相,而六部属焉”,即,六部是内阁的下属,是为内阁办事的。
虽然有所夸张,但却充分展示了如今内阁的权势。
五年前,内阁大学士黄淮、金幼孜都离开了内阁,而后又补入了一位尚书、一位右都御史。
二品高官入内阁,为群辅,位在首辅、次辅之下,这等境遇,让天下士林为之震动。
对内阁愈发敬畏。
文渊阁占地愈多,却仍然稍显逼仄,概因其文书之多,远胜往昔。
外间文书小吏颇为繁忙,一迭迭奏章被分门别类抱进抱出,虽不乱,却匆匆,幸好制度明确,颇有条理,才极少有错漏之事。
首辅独占一间,其后左右各坐二三人,各理其事,若有疑难,则由首辅核准裁决,若有大事则众人齐聚文渊阁中堂,进行商议,以定票拟。
文渊阁中堂,李显穆端坐长桌之后,左右各堆着一堆奏章,不时有书吏将右侧的奏章带走,又不断有书吏往左侧添上新的奏章。
许是有些累,李显穆停下笔,轻轻揉了揉眼睛,站起身向外走去,入目所见,皆是红墙黄瓦,富丽堂皇。
仰首望天,高高的宫墙衬的这偌大皇宫如一口四方井,将人紧紧束缚在这里。
他眉眼间带着消散不去的寒意厉色,仿佛深深刻在心头。
“永不曾停下啊。”
李显穆微微感慨着,治理天下当真是艰难,永远都有层出不穷的问题,解决了一个问题,立刻就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冒出来。
“元辅。”
有书吏自身后来,轻声呼唤。
李显穆回身望去,书吏谦卑躬身,垂首抱拳,“方才御前总管来传口谕,陛下请诸位学士至华盖殿,有要事相商。”
李显穆微微点头,示意自己知晓,抬眼看去,另外几位内阁大学士已然从各堂阁中走出,几人汇在一起,往华盖殿而去。
入殿后,一看皇帝脸色,几人就知道不是坏事。
皇帝朱瞻基立在上首,数年皇帝生涯,让他眉宇间多出几分凛然不可侵犯之意。
数年以来,李显穆固然威势愈盛,但皇帝更是威严盛隆,在政事上,他大部分委任给大臣,只参与重要决策。
但在军事上,他丝毫不假手他人,两次御驾亲征北巡,让瓦剌、鞑靼望风而逃。
又整治三大营,在军队中安插忠诚于自己的亲信,用联姻等方式笼络高级勋贵,牢牢握着兵权,是真正的实权皇帝。
见众人走进,朱瞻基当即命内侍给李显穆,以及上了年纪的杨士奇搬椅子过来,不多时,六部尚书、左右都御史等人也入了殿中,基本上大明朝中枢高级官员,齐聚一堂。
见人到齐了,朱瞻基当即笑道:“今日召诸卿前来,是有一件比较重要的事,皇太子年岁渐长,朕、太后、皇后,都想着让他出阁读书,不知诸卿可有什么想法?”
殿中群臣闻言顿时神色皆一凛,唯有李显穆微微眯起了眼。
皇太子朱祁镇实际上可以算是宣德二年生人,如今是宣德九年,满打满算,宣德九年过完,他八岁整,的确是可以出阁读书的年纪。
群臣之所以如此紧张,自然是因为,皇子出阁读书之事,涉及到未来的权力之争。
若是能提前在太子这里布局,或许未来就有奇效。
虽然皇帝现在春秋鼎盛,但提前落子总是没错的。
无论内阁还是部堂,都有人蠢蠢欲动。
倘若能成为太子师,那未来就是帝师,有了这重身份,未来未必不能和首辅李显穆一比。
李显穆则认为自己大概率做不成这个帝师。
除非皇帝一定要选择他。
但皇帝大概率也不会选择他。
朱瞻基虽然极度信任他,但这种信任依旧是有上限的,作为一个登基九年、十年的皇帝,平衡朝堂实力刻在他的骨子里。
就比如,他可以让李显穆放开手脚去做事,给予一切支持,但却不可能让李显穆把反对派全部处理掉。
是以李显穆不曾先开口。
李显穆对朱瞻基是有些误会的。
朱瞻基是真的考虑过让李显穆做皇太子老师的,但是又想到李显穆平日里已然很忙,不一定能有时间教导皇太子蒙学,于是最终放弃了。
打算等到皇太子十五岁左右,能正式开始接触政事,再由李显穆教导,当初他也是这个年龄,才由李显穆开始正式教导。
礼部尚书径直出言道:“陛下,臣以为当选饱学鸿儒,为皇太子教授,先以圣人之言,定其初生之心神,以正其魂、其骨。”
李显穆眉头缓缓舒展。
饱学鸿儒!
礼部尚书说出这四个字,就是为了把李显穆排除出帝师行列,因为李显穆虽然是圣人子弟,也曾经连中小三元、大三元,但他还真的算不上鸿儒,而一直以经世致用的面容面对天下。
从他出世以来,从来没有在学术方面发表过任何一篇文章,也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一场经典讨论,甚至在传播心学这方面,他所做的也是利用政治影响力来推动。
真正传播心学思想的一直都是他师兄王艮。
虽然,这都是李显穆装的,他是故意不在学术上发挥天赋,要知道,在李祺使用半圣之姿后,李显穆最强的一项天赋就是学术,政治天赋反而稍逊。
但世人不知道。
真以为他不擅长这方面。
李显穆自然不可能现在暴露,于是微微垂下头去,他不会去争皇太子的帝师资格。
没有意义。
成为帝师,是为了潜移默化的向未来的皇帝施加影响力,可如今已然是宣德九年,明年朱瞻基就会驾崩,一年时间,根本来不及施加什么影响力。
后宫可是有太后和皇后的,再怎么比,难道还能比得过那两位吗?
未来皇帝的态度,实际上取决于太后、皇后的态度。
李显穆所考虑的实际上就是后来的张居正和李太后合作的模式,皇帝服从太后,于是皇权在李太后手中,李太后再通过制度,把权力让渡给内阁首辅。
一开始高拱,但是高拱失去了李太后的信任,于是灰溜溜的被赶回了老家,张居正则被信任,得以掌权,这就是万历年间的权力运作模式。
李显穆预计,若是皇帝朱瞻基驾崩,极大概率会将政权移交给张太后和孙皇后,而后设立辅政大臣。
那他真正该施加影响力的,应当是张太后,孙皇后大概率是难以合作的,毕竟现在孙光宗还在南京城里关着呢。
“鸿儒吗?”
皇帝重复了一句,轻轻点头,“是应当寻鸿儒教导,除了鸿儒之外,朕也会亲自教导他,还要为他多选几个师傅,当初太宗皇帝为朕选了很多师傅,才有朕今日,如今朕也要让皇太子,文武双全,未来能克继大统。”
见到自己的意见被采纳,礼部尚书顿时欣喜,当即便举出几个例子,皆是在朝野之中,颇有盛名的鸿儒。
见李显穆一直沉默,其余人也忍不住开始推荐自己认为合适的人选。
“老师觉得呢?”
皇帝一开口问李显穆,其余人顿时安静了下来,李显穆平静着、施施然道:“皇太子年纪尚幼,心性不定,如今所学的应当是正心之法,使皇太子未来能有慨然于振作天下之心。
国朝选士,是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。
培养君王则更是如此,让隋朝二世而亡的隋炀帝,并不是没有才华、并不是没有才能,可却没有德行,于是肆虐天下,最终导致国败社稷亡。
臣并无太多推荐,只请陛下以此选士。”
朱瞻基含笑朗声道:“老师所言,朕都记在心中了,当真是明言之理,诸位卿家今日可再推荐些人,朕思索一番再说。”
殿中群臣又开始分别推荐自己派系,或者和自己有关系的人。
当然,这些被推荐的人,其实大多数都没问题,教个七八岁的小屁孩而已,以这些人的水平,只要智力中等偏上,教出个举人、进士,都没问题。
……
朱瞻基带着一大群推荐名字回到了后宫,将今日之事讲给孙皇后,又将朝臣所推荐的人选一一讲给孙皇后听。
恰在此时,朱祁镇也进了皇后宫中,拜过了皇帝和皇后,颇为好奇的问道:“父皇、母后,这是什么?”
朱瞻基摸摸朱祁镇的头,温声道:“这是父皇给你找的未来老师,日后你就要跟着他们读书学习了。”
“里面可有内阁首辅守正公吗?”
“哦?你想跟着守正公学习?”
朱瞻基倒是有些惊讶,谁知朱祁镇连忙摇了摇头,如同一只拨浪鼓一样,连声拒绝道:“儿子不要跟着守正公学习,千万不要。”
这下朱瞻基直接皱起了眉头,“儿子,你为什么不想跟着守正公学习,他虽然不是鸿儒,但才能是毋庸置疑的。”
朱祁镇有些不好意思道:“他太凶了,每次在宫中、宴会上见到他,都凶凶的,不苟言笑,让人很害怕。”
朱瞻基闻言一愣,紧皱了眉头顿时舒展开,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,他万万想不到会是这个原因。
本来还以为是有人和皇太子说了些什么,他虽然暂时放弃了让李显穆当帝师的打算,但维持两人之间良好的关系,保持初步的信任,还是要做的。
他自然知道自己儿子说的很正常。
李显穆这些年在朝廷之上,厉行澄清吏治,这可不是一件老好人能做出来的事,是以终日不苟言笑、威严日盛,顾盼之间,回眸之时,满是压迫,即便是那张帅脸也救不了这种精神上的威压。
平日里,纵然是其他的官吏们也畏之如虎,更不要说朱祁镇这个小孩了,怕是见过一次之后,怕是能止小孩夜啼。
孙皇后见朱祁镇所说,反而显出笑容来,“既然皇儿不愿意,那就不让阁老当老师,我大明能人辈出,难道还找不出几个能教得了皇儿的人吗?
况且,陛下才是这世上最好的老师,皇儿跟在陛下的身边长大,就像是陛下跟在太宗皇帝身边长大,未来必定是一代明君,和我大明的历代先帝一样。”
听孙皇后提起太宗皇帝,朱瞻基顿时陷入了回忆之中,他这一身本事,有七成都是太宗皇帝教的,爷孙两的感情是真的好。
他轻轻摸了摸朱祁镇的脑袋,眼中满是柔色,“父皇为好好教你的,未来还要把大明江山都交到你的手中。”
朱祁镇闻言顿时高高挺起了胸膛,中气十足的说道:“父皇母后放心,儿子日后必然会向列祖列宗学习,北御蒙古,南镇诸夷,儿子以后也要想太宗皇帝和父皇那样,御驾亲征,让瓦剌和鞑靼知道,什么叫做天威不可冒犯!”
朱瞻基听着朱祁镇这中气十足,又颇有志向的小儿言语,顿时大声笑起来,边笑边道:“好,朕的儿子果然像朕,有志气,当初朕十几岁就跟着太宗皇帝北征,等你十几岁的时候,朕也带着你北巡,教给你如何派兵布阵,也许日后,你也能成为太宗皇帝那样的将军皇帝呢。”
不得不说,良好的传统是会继承的。
大唐每一任皇帝都梦想成为唐太宗,希望能够再现贞观盛世。
而大明朝,朱棣五征蒙古带来的影响力余波,十年后仍旧经久不散,朱瞻基两次北巡,在长城外和蒙古对拼,便是深受朱棣的影响。
如今一个八岁稚童,眼见父亲、祖宗的丰功伟绩,也以御驾亲征,击破蒙古为志向。
当真是,薪火相传,以为圣光!
(本章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