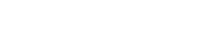建委主任的电话刚掛,丁义珍就拨通了秘书处。
“通知工信局、財政局、发改委,明天一早八点半,上我办公室开会。议题只有一个——產业升级。”
他把手机扣在桌上,目光落在电脑屏幕右下角的时间上:凌晨三点十七分。窗外的京州城早已沉入寂静,只有市委大院门口那盏孤灯还亮著,照著一辆停了许久的黑色轿车。车牌尾號確实是“886”。
丁义珍没再看它。
他重新调出刚才被打断的城市规划图,手指在触控板上滑动,將南巷和幸福里两个片区的绿色標记缓缓缩小,接著放大整个城区的工业布局图。老厂区密布在西郊,锈跡斑斑的厂房像一块块陈年旧疤;东南方向倒是新划了几片开发区,可土地空置率超过六成。
“光修几条路,清几道沟,治不了根。”他自言自语,“钱可以压下去一次流程,压不住整个系统。得换个活法。”
他起身走到白板前,拿笔写下三行字:
**传统產业怎么救?**
**新兴產业怎么引?**
**政府该做什么,不该做什么?**
写完,他退后两步看了看,又在最后一行下面画了个圈。
更新不易,记得分享101看书网
天刚蒙蒙亮,会议室就坐满了人。周叔来得最早,拎著个黑皮文件夹,坐下后不紧不慢地掏出老镜。建委主任紧隨其后,进门时还搓著手,像是刚从冷风里钻进来。
“各位,”丁义珍开门见山,“昨天晚上,我们好不容易批下去的施工许可,系统权限又被锁了。”
眾人面面相覷。
“技术组查了,不是故障,是人为调整了访问组別。”他顿了顿,“我不想知道是谁干的。我现在只想告诉所有人——如果我们还陷在这种你掐我、我卡你的拉锯战里,京州十年都翻不了身。”
周叔推了推眼镜:“你是想动大棋了?”
“对。”丁义珍点头,“民生工程必须推,但不能只靠我一个一个去盯。我们要做的,是让整个城市的发展逻辑变过来。”
他打开投影,调出几张照片:苏州工业园的自动化流水线、深圳科技园里年轻人围著一台3d印表机討论方案、寧波一家老牌纺织厂改造后的智能车间。
“这些地方十年前什么样?跟我们现在差不多。但他们敢转,肯投,政策跟得上。”他指著其中一张图,“这家机械厂,老板去年贷款换了整套数控设备,今年订单接到手软,连俄罗斯的代理商都找上门。”
工信局局长皱眉:“可我们这儿的企业,多数还在用九十年代的工具机,让他们一步跨到智能化,怕是受不了。”
“没人说一步到位。”丁义珍说,“我的想法是两条腿走路——一手抓传统企业技改,另一手孵化新兴產业。先易后难,先试点再铺开。”
財政局副局长立刻接话:“技改要补贴,孵化要园区,哪样不要钱?去年財政结余才几个亿,您这一开口,怕是要砸进去几十个。”
周叔这时开了口:“钱不是问题,问题是槓桿怎么打。”他翻开文件夹,“我算过一笔帐,如果採用『以奖代补』方式,企业完成技改並通过验收后再给资金,財政风险可控。而且,只要產能提升,税收自然上来,形成良性循环。”
“举个例子,”他抬头看著眾人,“一家中型机修厂投入五百万升级设备,效率提升40%,一年能多赚三百万。按25%所得税算,三年就能回本,政府还能多收七八十万税。这笔帐,值不值?”
会议室安静了几秒。
建委主任摸著下巴:“园区这块,倒是可以盘活閒置地块。东新区有两块地掛了两年没人要,要是定好產业方向,搞定向招商,未必起不来。”
“那就定了。”丁义珍拍板,“第一阶段,选三家国企机修厂、两家民营纺织厂做技改试点,市里配套服务专班,一对一帮扶。同时启动东新区智能製造產业园规划,年底前完成基础设施建设。”
散会后,周叔留了下来。
“你爸当年在香江,也是这么干的。”他一边收拾材料一边说,“別人走私电器,他带著甫光船队运的是工具机、模具、图纸。那时候谁懂什么叫產业升级?可他愣是靠著一批旧设备,建起了第一条生產线。”
丁义珍笑了笑:“他是闯关的,我是守城的。”
“一样的胆子,不一样的打法。”周叔戴上帽子,“不过有一点相通——都得让人看到希望。光讲道理没用,得让他们看见钱能挣,日子能好。”
两天后,丁义珍带队出发,去了苏州和深圳。
考察途中,隨行的一位副局长嘟囔:“人家底子厚,咱们抄不来。”
丁义珍听见了,没吭声。到了深圳一家智能装备公司车间,他指著正在组装的机械臂问负责人:“这玩意儿十年前贵吗?”
“贵啊,一套进口的七八百万。”
“现在呢?”
“国產化之后,不到两百万,性能还更强。”
丁义珍回头看了眼那位副局长:“听见没?他们也不是天生就有,是一步步换下来的。”
回程火车上,他拉著周叔和建委主任在餐车碰头。
“方案草擬一下,就叫《京州市產业升级三年行动草案》。”他说,“重点写清楚三条:一是技改补贴怎么发,二是园区怎么建,三是服务专班怎么运作。”
周叔回头问:“刘志军那边……要不要提前通个气?”
丁义珍沉默片刻:“不用。等方案成型,直接上会。他要是反对,就让他当著所有人的面说理由。”
三天后,草案初稿摆在了丁义珍桌上。
他还没来得及细看,秘书敲门进来:“几家试点企业负责人到了,在小会议室等著。”
丁义珍拿著文件走进去时,屋里已经坐了五个人。最边上那个穿旧夹克的中年男人他认识——红星三厂的厂长李卫国,他爷爷曾经工作过的老厂。
“丁书记,”李卫国开门见山,“投五百多万换设备,我信您说的是好事。可万一市场不行,贷款还不上,厂里三十多个工人怎么办?”
其他人纷纷点头。
丁义珍把草案放在桌上,翻开一页:“第一年完成技改並通过验收,市里补贴30%。第二年如果订单不足,政府牵头对接央企和大型製造企业的供应链採购。”
他抬眼看著李卫国:“你厂子原来给矿山机械做配件,现在能不能接新能源汽车部件的单?只要设备达標,我亲自给你打电话,联繫寧德时代的技术团队来做认证。”
屋里一下子静了。
“还有,”丁义珍继续说,“每个试点企业,由一名市领导包干联繫,每月至少上门一次,问题当场协调。你们不用担心审批卡壳,也不用怕没人撑腰。”
李卫国低头搓了搓手:“要是真这么干……我愿意带头试。”
其他几个人也开始低声议论。
丁义珍站起身:“我知道大家有顾虑。但路总得有人先走。我不敢说百分百成功,但我敢保证——只要你们实打实干,政府绝不会撒手不管。”
会议结束已是傍晚。
他回到办公室,把试点企业名单贴在白板上,用红笔圈出第一批五家。窗外,夕阳正落在远处一座老烟囱上,砖红色的墙体映著金光,像被点燃了一样。
他拿起电话,拨通秘书:“明天安排个时间,我要去红星三厂看看他们的老车间。”
话音未落,桌上的平板忽然震动了一下。
是系统提醒:东新区审批系统权限再次异常,访问受限。
“通知工信局、財政局、发改委,明天一早八点半,上我办公室开会。议题只有一个——產业升级。”
他把手机扣在桌上,目光落在电脑屏幕右下角的时间上:凌晨三点十七分。窗外的京州城早已沉入寂静,只有市委大院门口那盏孤灯还亮著,照著一辆停了许久的黑色轿车。车牌尾號確实是“886”。
丁义珍没再看它。
他重新调出刚才被打断的城市规划图,手指在触控板上滑动,將南巷和幸福里两个片区的绿色標记缓缓缩小,接著放大整个城区的工业布局图。老厂区密布在西郊,锈跡斑斑的厂房像一块块陈年旧疤;东南方向倒是新划了几片开发区,可土地空置率超过六成。
“光修几条路,清几道沟,治不了根。”他自言自语,“钱可以压下去一次流程,压不住整个系统。得换个活法。”
他起身走到白板前,拿笔写下三行字:
**传统產业怎么救?**
**新兴產业怎么引?**
**政府该做什么,不该做什么?**
写完,他退后两步看了看,又在最后一行下面画了个圈。
更新不易,记得分享101看书网
天刚蒙蒙亮,会议室就坐满了人。周叔来得最早,拎著个黑皮文件夹,坐下后不紧不慢地掏出老镜。建委主任紧隨其后,进门时还搓著手,像是刚从冷风里钻进来。
“各位,”丁义珍开门见山,“昨天晚上,我们好不容易批下去的施工许可,系统权限又被锁了。”
眾人面面相覷。
“技术组查了,不是故障,是人为调整了访问组別。”他顿了顿,“我不想知道是谁干的。我现在只想告诉所有人——如果我们还陷在这种你掐我、我卡你的拉锯战里,京州十年都翻不了身。”
周叔推了推眼镜:“你是想动大棋了?”
“对。”丁义珍点头,“民生工程必须推,但不能只靠我一个一个去盯。我们要做的,是让整个城市的发展逻辑变过来。”
他打开投影,调出几张照片:苏州工业园的自动化流水线、深圳科技园里年轻人围著一台3d印表机討论方案、寧波一家老牌纺织厂改造后的智能车间。
“这些地方十年前什么样?跟我们现在差不多。但他们敢转,肯投,政策跟得上。”他指著其中一张图,“这家机械厂,老板去年贷款换了整套数控设备,今年订单接到手软,连俄罗斯的代理商都找上门。”
工信局局长皱眉:“可我们这儿的企业,多数还在用九十年代的工具机,让他们一步跨到智能化,怕是受不了。”
“没人说一步到位。”丁义珍说,“我的想法是两条腿走路——一手抓传统企业技改,另一手孵化新兴產业。先易后难,先试点再铺开。”
財政局副局长立刻接话:“技改要补贴,孵化要园区,哪样不要钱?去年財政结余才几个亿,您这一开口,怕是要砸进去几十个。”
周叔这时开了口:“钱不是问题,问题是槓桿怎么打。”他翻开文件夹,“我算过一笔帐,如果採用『以奖代补』方式,企业完成技改並通过验收后再给资金,財政风险可控。而且,只要產能提升,税收自然上来,形成良性循环。”
“举个例子,”他抬头看著眾人,“一家中型机修厂投入五百万升级设备,效率提升40%,一年能多赚三百万。按25%所得税算,三年就能回本,政府还能多收七八十万税。这笔帐,值不值?”
会议室安静了几秒。
建委主任摸著下巴:“园区这块,倒是可以盘活閒置地块。东新区有两块地掛了两年没人要,要是定好產业方向,搞定向招商,未必起不来。”
“那就定了。”丁义珍拍板,“第一阶段,选三家国企机修厂、两家民营纺织厂做技改试点,市里配套服务专班,一对一帮扶。同时启动东新区智能製造產业园规划,年底前完成基础设施建设。”
散会后,周叔留了下来。
“你爸当年在香江,也是这么干的。”他一边收拾材料一边说,“別人走私电器,他带著甫光船队运的是工具机、模具、图纸。那时候谁懂什么叫產业升级?可他愣是靠著一批旧设备,建起了第一条生產线。”
丁义珍笑了笑:“他是闯关的,我是守城的。”
“一样的胆子,不一样的打法。”周叔戴上帽子,“不过有一点相通——都得让人看到希望。光讲道理没用,得让他们看见钱能挣,日子能好。”
两天后,丁义珍带队出发,去了苏州和深圳。
考察途中,隨行的一位副局长嘟囔:“人家底子厚,咱们抄不来。”
丁义珍听见了,没吭声。到了深圳一家智能装备公司车间,他指著正在组装的机械臂问负责人:“这玩意儿十年前贵吗?”
“贵啊,一套进口的七八百万。”
“现在呢?”
“国產化之后,不到两百万,性能还更强。”
丁义珍回头看了眼那位副局长:“听见没?他们也不是天生就有,是一步步换下来的。”
回程火车上,他拉著周叔和建委主任在餐车碰头。
“方案草擬一下,就叫《京州市產业升级三年行动草案》。”他说,“重点写清楚三条:一是技改补贴怎么发,二是园区怎么建,三是服务专班怎么运作。”
周叔回头问:“刘志军那边……要不要提前通个气?”
丁义珍沉默片刻:“不用。等方案成型,直接上会。他要是反对,就让他当著所有人的面说理由。”
三天后,草案初稿摆在了丁义珍桌上。
他还没来得及细看,秘书敲门进来:“几家试点企业负责人到了,在小会议室等著。”
丁义珍拿著文件走进去时,屋里已经坐了五个人。最边上那个穿旧夹克的中年男人他认识——红星三厂的厂长李卫国,他爷爷曾经工作过的老厂。
“丁书记,”李卫国开门见山,“投五百多万换设备,我信您说的是好事。可万一市场不行,贷款还不上,厂里三十多个工人怎么办?”
其他人纷纷点头。
丁义珍把草案放在桌上,翻开一页:“第一年完成技改並通过验收,市里补贴30%。第二年如果订单不足,政府牵头对接央企和大型製造企业的供应链採购。”
他抬眼看著李卫国:“你厂子原来给矿山机械做配件,现在能不能接新能源汽车部件的单?只要设备达標,我亲自给你打电话,联繫寧德时代的技术团队来做认证。”
屋里一下子静了。
“还有,”丁义珍继续说,“每个试点企业,由一名市领导包干联繫,每月至少上门一次,问题当场协调。你们不用担心审批卡壳,也不用怕没人撑腰。”
李卫国低头搓了搓手:“要是真这么干……我愿意带头试。”
其他几个人也开始低声议论。
丁义珍站起身:“我知道大家有顾虑。但路总得有人先走。我不敢说百分百成功,但我敢保证——只要你们实打实干,政府绝不会撒手不管。”
会议结束已是傍晚。
他回到办公室,把试点企业名单贴在白板上,用红笔圈出第一批五家。窗外,夕阳正落在远处一座老烟囱上,砖红色的墙体映著金光,像被点燃了一样。
他拿起电话,拨通秘书:“明天安排个时间,我要去红星三厂看看他们的老车间。”
话音未落,桌上的平板忽然震动了一下。
是系统提醒:东新区审批系统权限再次异常,访问受限。